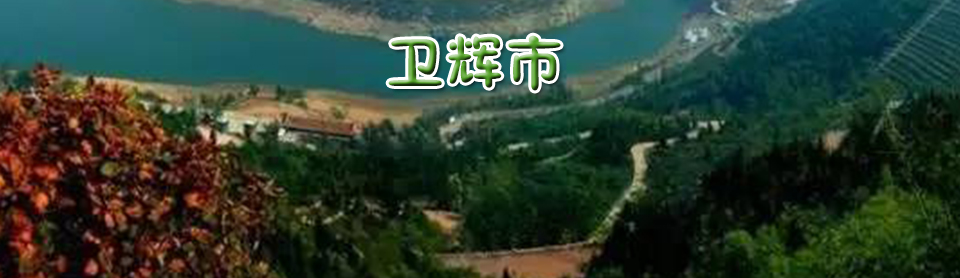卫河怀古那些年汲县卫河的老照片,是卫
杨凤瑞,汲县人,一九八零年毕业于汲县师范学校,现为卫辉市政协文史委研究员,卫辉古城开发专家组顾问。
我家住在卫河岸边,现在却没有《歌唱祖国》那样美好的意境。每天早晨和傍晚,我牵着雄赳赳、气昂昂的“黑贝”从古老卫河的河岸上走过,看着静静流淌的卫河,总会不由自主地在脑海中浮现昔日卫河的影像,想起往昔“一条大河波浪宽……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繁忙的水运场景,禁不住发出今不如昔的叹息。
二零一六年,汲县卫河上乐村水闸。
一九六零年,汲县卫河航运。
二零一七年,汲县卫河司湾村景。
卫河,是卫辉的母亲河,卫辉因卫河生辉而得名。她发源于辉县的苏门山和博爱的皂角树村,在新乡县合河村西合流,入卫辉后又有淇水、安阳河、汤河等十余条支流成梳齿状汇集而成,经山东、河北到天津汇入海河,她是豫北唯一属于海河水系的河流。卫河名称由古代清河、屯氏河、白沟、永济渠演变而来,分别为战国、汉朝、两晋、隋朝古称,唐宋时因是古时隋炀帝疏浚,又称御河,直到元明时才因流经卫国故地改称卫河。隋唐以来,卫河担负着大运河北段的漕运使命,源源不断地将南方的货物运达现在的京津冀地区,到明清时,往来新乡和天津间的货船多达七百余只,载重八吨以上的大船占到三分之一,船民约三千余人。卫辉作为豫北战略重镇,是扼守北上南下的咽喉要冲,卫河水运在卫辉之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二零一四年,汲县卫河李良屯春光。
五十年代末,汲县卫河附近的京广铁路。
二零一七年,汲县卫河毛楼河坡。
明清之卫辉,为豫北三府之一。万历皇帝之胞弟潞王在此封藩,北洋军阀之父袁世凯在此建有行馆,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在此出生。北京有故宫,卫辉有王府;北京有天安门,卫辉有望京楼;北京有景山,卫辉有煤山;北京有金水河,卫辉有玉带河;北京西北有燕山屏障,卫辉西北有太行叠翠……总之,北京有的,卫辉也有,所以素有“小北京”之称。陆地通京大道在德胜桥与水路卫河漕运交汇,造就了沿淀、德北、严光、板楼、官驿、地坛、熟肉火、下街、延寿宫和南北马市街城西北地带的繁华。
二零一七年,汲县卫河黑窑厂河坡。
五十年代末,汲县卫河渡口。
二零一六年,汲县卫河娘娘庙卫河桥。
古城第一个迎接黎明的,是德胜桥头人声鼎沸的水陆码头,脚夫河上河下忙着搬运各种包装的大小货物,车夫和挑夫将上岸的货物肩挑手拉移往货栈或城内,停在桥头南北的大小骡马车、牛驴车以及手推车,急不可耐地要运走装满的货物,河下“欸乃”的摇橹声与两岸纤夫逆流南下“嗨吁”的号子声交织在一起,打破了卫河一夜的沉静,整个河面犹如人体的静脉和动脉,又开始来来往往的流动。只有停泊在岸边的船只,船舱里的炊烟与东方的旭日一起袅袅升起;河边关闭了半夜的黑油门,此时也“吱吱呀呀”一扇扇打开;红黑蓝白的四角帐篷下,早已开张的小吃摊,摊主拼命地呼唤着买主光临;起的比谁都早的各色小狗四处流荡,激动地寻觅着似乎随时可得的食物……古城新的一天开始了。
二零一七年,汲县卫河府君庙河堤。
七十年代末,汲县卫河岸边一人家结婚拜堂仪式。
二零一六年,汲县卫河王奎屯村景。
经历短暂的平静,以德胜桥为中心又开始新一轮的灵动。西北和东南各地的客商经过与货栈掌柜一番艰难的讨价还价,又与前来讨生计的车主打起口水仗,接着在相互冤称“从未出过这样的价钱”声中装上货物运走;熄灭了炊烟的货船,赶紧乘着突如其来的西南风,扬帆启航;城里四关居民肩上担着水桶,纷纷下到河边汲水,南北马市街挑水自用的、卖水糊口的,脚步匆匆,络绎不绝;德胜桥通向“南通十省,北拱神京”高大牌楼的大路上,马蹄声碎,车轮滚滚,人欢马叫,好生热闹;推车挑担提篮的各式小卖,沿着河岸,顺着街巷,“卖糖堆儿喽,谁要糖堆儿!”“称葱吧,买蒜吧,萝卜韭菜蒜苗的!”“豆腐,码头嘞豆腐来了!”“黄豆芽绿豆芽,贺生屯嘞豆芽的!”“谁要麻糖,热里麻糖!”“烧红薯烧红薯,黄心儿红心儿烧红薯!”……形形色色的叫卖声不绝于耳;桥头钉鞋、卖鞋、打铁壶、焊暖壶、薅牙安牙、裁蹄钉掌……各类固定摊点,互相打着招呼,陆续做起新一天的生意。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事关民生的一切,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所需所要。中午时分,商贾们邀请各自的生意伙伴,走进又一春、德盛楼、品味斋、宴宾堂、汇贤居等老字号饭庄,看着沿街、沿河川流不息的人群或行船,品尝着色香味俱佳的菜肴,在觥筹交错中畅谈着生意,加深着友谊,偶尔也会八卦一些名人轶事,但绝不敢妄议朝政。
二零一五年,汲县卫河王奎屯河坡。
七十年代初,汲县卫河严光后街河坡。
二零一六年,汲县卫河石庄河坡牧羊人家。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阴云密布,无论是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无论是夏日炎炎,还是冰雪寒冬,卫河的德胜桥一带,下午总是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上午的故事,只有到了傍晚落黑,才会发现卫河夜色中的华丽风姿是何等妖娆卓约。当灰蒙蒙的苍穹尚未点缀闪亮的星星,四方的城门早已关闭,伸向护城河的吊桥高高升起,就连沿淀寨墙小东门外吕公堂的吊桥也早已升起;城内和沿淀的寨墙内一片死寂,没有丝毫的生气,达官贵族不愿与百姓为伍,习惯地过着属于他们的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德胜桥南北河里一艘艘船的桅杆上,高高地点上各色长长的灯笼,艄公坐在船舱外的甲板上,一边捧着大碗吃饭,一边操着南腔北调与邻船聊天;板楼街的客栈面河而居,门首红灯笼“张王李赵”的黑色大字,显示着不同的主人和风格,“来了,里面请!”店家招呼客商的高声叫喊,不时由深宅传出,再由河面发出回响,在夜空中久久回荡;马市街是最为繁华的所在,从德胜桥到西门桥,像牛梭弯一样漫长的街衢两侧,回民皮货商、太行山货商、蒙古贩马商、南蛮丝绸商……商贾云集,饭庄里灯火通明,继续着白天未能达成的生意,划拳行令,酒意方酣,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德北街是车夫、脚夫、杂役汇聚之地,但因有悦春楼等数家妓院的存在,到处笙歌曼舞,一片灯红酒绿,“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河犹唱后庭花,“商人重利轻别离”,浪迹江湖任潇洒;与城内达官贵族不同,沿淀寨墙内居住的多为盐商等富商巨贾,他们骄奢淫逸,雇佣的家丁打更值守,沿河的寨墙上,三五成群,挑灯巡逻,木梆铜锣的“梆梆”“哐哐”声划破夜空;由沿淀寨墙循河北望,河中的渔火犹如天空的银河,成倒“丁”字型的德北、马市街与板楼街,沿途灯火辉煌,加之吕祖阁传来的阵阵钟鸣,绝不逊色“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苏州夜景。古时城西北的富庶商业区,其繁华程度与今天地处新乡医学院一附院的健康路和学院西路极其相似,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那时是吃卫河,医院,那时有水的灵性,现在是旱地经营,眼前表面的繁荣却无吸引人的魅力。
二零一六年,汲县卫河东码头豆腐皮。
七十年代末,汲县卫河岸边豫北医专学生校内礼堂合影。
二零一七年,汲县卫河河园河坡。
当然,卫河带来的繁荣远不止这些。沿淀小南门外是巨大的怀盐场,它是面对东南地区的盐业集散地。北仓地势高凸,是囤积粮食的巨大仓储。北码头、东码头、南码头三个码头,是弥补德胜桥停泊紧张的不时之需......卫河给古卫辉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为带动当时一、三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卫河在严光至河园转弯处,随着河道变宽,水流趋缓,泥沙沉积,辽阔清澈的水面,碧波荡漾,成为卫辉“卫水拖蓝”的八景之一。每当夕阳西下,我们的先祖们站在卫河东岸,眺望如黛的远山,俯瞰拖蓝的卫水,目睹远行的航船,点点帆影在晚霞的映照下随波舞动,心旷神怡,其乐何及?
二零一六年,汲县卫河王庄河坡。
八十年代初,用卫河清淤挖出来的河沙填起来的汲县老体育场。
二零一七年,汲县卫河洪庄河坡。
时光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污水沟。两岸高楼拔地起,怎奈心中空悠悠。我竭力地追寻时光隧道,想让古老美丽的卫河重现今人面前,然而墨竭笔秃,孤陋寡闻,或因今不如昔的惆怅过于伤感,或为昔日的繁华难以尽情描述,或感数百年的历史此去久远,在不堪煎熬中拿起笔来,聊发胸臆。也许退去繁华、记忆殆尽的美丽卫河还会出现在我们眼前……
二零一六年,汲县卫河倪湾春光。
八十年代初,汲县卫河岸边市民闹元宵。
二零一六年,汲县卫河汲城卫河桥。
来源:咪饭视角
卫辉生活圈广告、新闻、营销热线
、
转载请注明:http://www.weihuizx.com/whsxs/85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