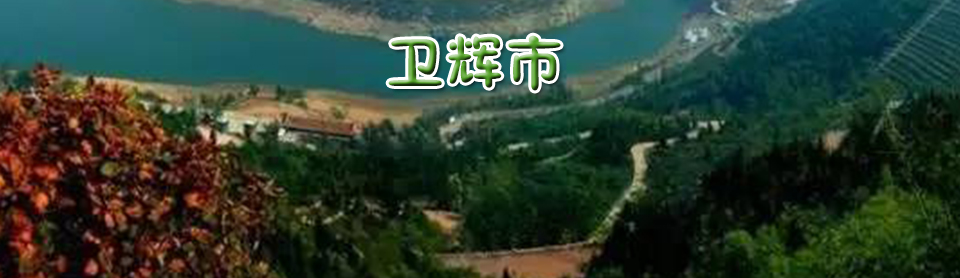卫辉古碑研究卫辉的ldquo古悬
卫辉的“古悬洞”与“罗成庙”
《乾隆汲县志》有两条记载,与隋末唐初名将罗仕信有关。即:
卷二《舆地志下·山川·古悬洞》:“在西北戴村广泽王庙东。其洞空旷,可容千人。元时有人避兵于内,今碓磨遗迹尚存。”
卷四《建置下·祠庙·广泽王庙》:“俗呼罗大王庙。在城西二十里戴村古潭上。王名士信,唐高祖时名将,累立战功,后以刘黑闼攻陷其所守城,不屈而死。卫人为立庙。遇旱灾,祷之辄应。宋宣和初,勑赠广泽王。金辽时末兵乱,颇显神灵。元至元年大旱,乡民敬祷于神,甘泽立降,因服修饰殿宇。孙庵有记。”
志书中的记载非常明确,言之凿凿,应该述有所据。民国河北道时,曾在卫辉居住八年,广搜河朔金石的顾燮光在《河朔访古新录》中记载“(汲县)县北二十里戴村广泽王庙,始建失考。有元至元十八年三月《大元国重建广泽王庙记》,缘庵谨记,牛居仁书。”可见,《乾隆汲县志》中“古悬洞”与“广泽王庙”两个条目之源大概率应为这通碑。
那么,曾经辉煌一时的“古悬洞”与“广泽王庙”,现在还有痕迹可寻吗?顾燮光所探访到的《大元国重建广泽王庙记》碑是否尚存人间?
一月十六日下午,在卫辉暴旭华老师的指引下,我们一行探访卫辉西戴村,不仅找到了“广泽王庙”的具体位置,而且在院西南偏僻之处发现了《大元国重建广泽王庙记》残碑的遗存。
该庙位于西戴村村南黄土岗之上。西北太行雄峙,正南沟壑俯瞰,沟底稍东即“古悬洞”旧址,庙西跨壑大桥凌空欲翔。此庙正房一座,配房二所,皆为现代之物。檐下有泥塑骏马,奋蹄昂首,颇有气势;只是侍马军士略显臃肿,颇显俗气。
院之西南侧有一断碑,漫漶严重,字迹不清,用水泥糊在底座之上,周围荆棘丛生,杂物堆积,甚不显眼。此处本就偏僻荒凉,此庙又残破不堪,加上此碑貌不惊人,故而长久不为人所知。仔细摩挲辨识,发现该碑即顾燮光曾经记载的《大元国重建广泽王庙记》。
此碑已残,仅余下部。高70厘米,宽61厘米,厚20厘米。碑阳正文四边有缠枝花饰。正文残留18行,每行残留22字左右。不见碑题。碑末有“至元十五年冬二日,逊庵谨记”“牛居仁书,男庭瑞刊”“(至元十八年)三月初九清明日,维那头石瑚立石”等,可知撰文、书丹、立碑者信息。从上边的断痕看,乃人为破坏所致。
该碑残留文字如下:
……□□□古老□云:神兴于唐,姓罗氏,讳仕信,本邑仙翁山
……□有功。唐贞观间,加聀赐粟。神赈济贫民,莩者得甦,乡里
……□□西北二十里戴村西古潭之上,郡人香火,绳绳相継
……□□□□粤宋宣和初,郡人告额于上,勑赠号曰
……□□□□以相侵夺。有朝歌寨王相公率兵二千至西山
……□□□□,□兵于内,招之不降。王兵击之,七日,洞欲陷,有
……□□胡兴、胡德常等默祷于神。须臾,王兵乃见西南山阜
……□□幼者观望□。旋共入庙中,众谢曰:“皆神之所佑也。”若
……庚戌岁,从春至夏,大旱。乡民敬祷于神,甘泽复降。有社长
……□□□□修廊庑。厥后,胡惠海、胡青、胡德、胡进等补塑
……□□聚□□□□协助。修饬殿宇,稍成伦序。太行倚其北
……恐后湮没。朝烟暮霭,千态万壮,而不可穷。间有到者,皆称
……□□□□。□磨翠珉,俾刊诸石,永传不朽,可否。众皆诺。于
……□□始□□业。请余作记。予知其心,不□乃为之叹曰:夫
……□□□□□神□□于民,祈祷感应,皆可发扬而推美之。
……□□□至元十五年冬二日,逊庵谨记。
……牛居仁书,男庭瑞刊。
……三月初九清明日,维那头石瑚立石。
碑中主要记载罗大王的灵应之事。一者,“有朝歌寨王相公率兵二千至西山”“□兵于内,招之不降。王兵击之七日,洞欲陷”“胡兴、胡德常等默祷于神”“须臾,王兵乃见西南山阜”“旋共入庙中,众谢曰皆神之所祐也”,把断断续续的记载串连起来,一段历史事实逐渐清晰。在元初兵乱之际,一支义军曾藏身“古悬洞”达七日之久而坚不投降。在“洞欲陷”之际,众人“默祷于神”而神兵(罗仕信率兵)从“西南山阜”出,解除了众人之难。此亦即《汲县志》“元时有人避兵于内”记载的由来。二者,“庚戌岁,从春至夏,大旱”“乡民敬祷于神,甘泽复降”,乡人为感谢神恩而葺庙立碑,“□磨翠珉,俾刊诸石,永传不朽”。
碑文的内容并不复杂,虽然仅余半石,但勉强可读。不过,其只言片语之中保存的历史文化信息却十分丰富,令人兴奋。如“唐贞观间,加聀赐粟”“粤宋宣和初,郡人告额于上,敕赠号曰”,可见宋宣和初年,宋徽宗曾给此庙赐额赠号,其号应为“广泽王”;但此事件,史书无载,故而碑中所记有补史之功。另外,该庙虽然始建失考,但既然在宋宣和初“告额于上,敕赠号曰”,说明宋宣和初年该庙已为大庙,香火极盛;否则,也不可能“告额于上,敕赠号曰”。又如“神兴于唐,姓罗氏,讳仕信”,明确指出所祀之神为初唐名将罗仕信,而不言罗成。罗仕信乃历史人物,《旧唐书》《新唐书》皆有传,其籍贯、仕历、功绩、结局等十分明确清晰;而罗成乃《隋唐演义》等小说中虚构的形象,其人物活动的脉络虽有历史的影子,但整体上仍属于艺术加工,不是信史。但文学的魅力和传播功能远非史书可比,当地传说庙下的古潭即罗成被苏定方射杀之处,当地人至今不许唱有关罗成落难的戏目,对罗成的勇敢、忠义颇为敬重。
其实,最令人疑惑和感兴趣的是首行末“神兴于唐,姓罗氏,讳仕信,本邑仙翁山”。首行至此而止,次行上部缺失,“本邑仙翁山”之后是什么内容,已难以知晓了。按照碑传的行文规律,“本邑仙翁山”处应该叙述罗仕信的籍贯,由于此处的戛然而止,反而给人们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难道罗仕信是“本邑仙翁山”人?(《唐书》明确记载罗仕信乃齐州历城人)亦或此支罗氏与“本邑仙翁山”有关?甚或罗仕信助李世民平定河北时曾鏖战于“本邑仙翁山”?也许罗仕信真的葬身于庙前的古潭?(罗仕信卒于洺水之战,洺水在邢台沙河市秦王湖一带;葬於北邙山)
可惜的是,该碑的上半截已杳无踪迹,亦无拓本、录文留存。若能有完整的录文,历史的某些面目就会变得清晰。这对研究唐初李世民征讨刘黑闼事件与卫辉的关系,卫辉西戴村、唐庄仙翁山地区的罗成故事传说的形成和发育,都有重大的参考意义。顾燮光晚年曾著《河朔金石文字新编》,专录诸书未著录之碑,但未见该碑的影子,可见当时顾燮光亦未见到此碑,实在令人遗憾。
碑中第九行有“庚戌岁,从春至夏,大旱。乡民敬祷于神,甘泽复降”的记载。“庚戌”两字比较清晰,不会有错。按历,至元十五年()之前的“庚戌岁”为元海迷失后称制二年(),二者相差近30年,似不太可能。故笔者怀疑“庚戌”乃“甲戌”(至元十一年,)之误。“庚”有异体,即“广”内为“甲”;书丹者或误把“甲”书为“庚”了。即便如此,至元十五年()撰文已成,至元十八年()三月清明之日才立碑,亦可见民生之艰难。
汲县的仙翁山一名仙山,在县西二十里山彪村,上有葛仙洞。《山西通志·万泉县·桃花洞》:“在孤山南麓。曩多桃树,故名。相传唐罗士信隐此。元刘仙翁海亦羽化于此,有登仙石遗迹。”可见在太行之域有罗士信隐居仙翁山、桃花洞的记载,说不定卫辉山彪的仙翁山、唐庄的桃花源亦与罗士信的隐居有关呢。汲县的仙翁山乃晋、秦、豫、冀交会之处,地处要冲,李世民征战河北,鏖战于此,应该是可信的。
碑石无价,残碑断碣皆是历史。爱好者要养成敬畏文字的习惯,研究者更应如此。庙前的“古潭”“古悬洞”已随着开山造田消失了,那是没办法的事情。但西戴村临近某采矿公司,村中居户日渐减少,千年古庙可不要随着矿山的开发而烟消云散啊。若真的有那么一天,请铲下留情,把那块《大元国重建广泽王庙记》碑保护起来,放到博物馆中,当后人再谈到罗仕信与罗成、古潭与“古悬洞”、仙翁山与葛仙洞时,多少有点凭据,也算是给历史留下一点记忆吧。
霍德柱
转载请注明:http://www.weihuizx.com/whsxs/78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