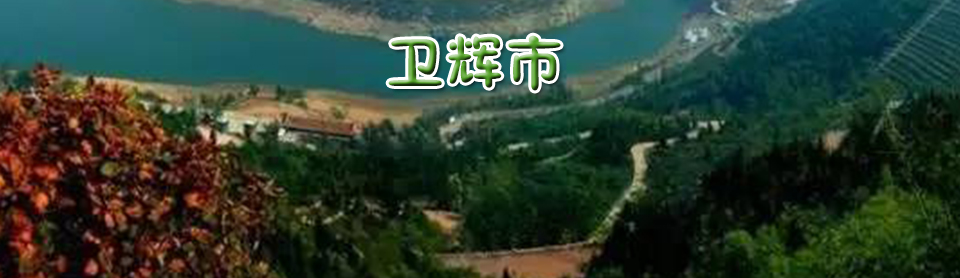安静执着追忆我的父亲全国劳模杨朝山
这是在北京参加全国劳模会议时唯一的一张纪念照(右数第二位)
父亲杨朝山少年参加革命,地下情报员。年,正式成为革命者一员,年,保送白求恩医科学校学习军医,战时吃紧,半年学习就奔赴战场,未颁发毕业证。父亲履历上他始终坚持填写的是高小毕业。年,安阳解放,医院四分院留驻安医院。年10月,医院调入建立平原省干部疗养院。年,他任放射科负责人,后任主任,直到离休。
我的家中有4位新中国的功臣,一位是我的爷爷杨逢春,一位是我大伯杨其山(时间久远不能确定正确,小名连连),一位是我的外祖父还有过世不久的父亲杨朝山。我的爷爷和大伯因为听到他们的故事很少,我只了解我爷爷曾是一位河北地下联络员,解放后被党中央政府安排为河北省副省级领导,但未上任,解甲归田,自此与世无争。大伯在解放石家庄的战役中牺牲,在部队是一位连级干部,牺牲后遗体就地掩埋,成为无名烈士,片言只语无法真实记录他们的英雄事迹,这里只能谈一下我比较了解的我的父亲杨朝山。
我的父亲生于年10月28日,卒于年9月8日,新医院建院年庆典前夕。是年5月16日,他不小心摔倒,造成股骨颈骨折,术后恢复中突然病逝,享年89岁。
父亲祖籍是河北省深县(深州市)清辉头村,那里至今也不是一个富裕的村庄。我的爷爷叫杨逢春,在他们村是一位十分有威望的族长,1米8多的个子,人高马大,长着一把圣诞老人似的连鬓大胡子,很气派很有威严。解放前他另一不为人知的身份是名地下党员,他年入党,是共产党地下情报联络站河北区站长,爷爷识字比较少,信件看不太懂。我父亲少年时给地主打短工,没有文化,党组织就秘密安排我父亲上了学,高小毕业,这样可以帮爷爷看信的内容,同时他也为联络站传递情报,这样我的父亲也就早早地参加了革命。我的父亲很少主动跟我们讲他小时候送情报的情节,只是说就像《鸡毛信》书上描写的那样,也常常受到盘查,不过每次都有惊无险,化险为夷了。情报有时是口信,多数是信件,有时以鸡毛信的形式传递的,鸡毛信表明情报的保密和重要程度,级别是鸡毛的根数表示的,父亲讲过,一根鸡毛或者两根鸡毛的比较常见,三根鸡毛的属于顶级绝密的信函,这样的也不少,当然也必须极其重视,严格保密,这说明情报来源于高级别的官员或者重特大情报。
父亲的党性原则十分强,对于党的秘密,始终不会透露丝毫,每一份情报内容我父亲都会念给爷爷听,一旦需要销毁就必须以口信的方式传递,但是他小小年纪从来没有向外透露一个字,他选择的是对这份崇高事业的执着和敬仰,始终坚守党的保密制度,这也许是后来造成他在生活中惜字如金的生活习惯。就包括后来我们道听途说的所谓“小道”消息,向他求证,他总是默不作声或笑而不语,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任何相关内容。虽世事变迁,也未改变他曾经宣读的誓言。
年,父亲经组织安排前往县里上中学继续深造,不到一年时间父亲就离开学校也是组织秘密安排,也不知道执行了什么任务,父亲从未提及。由于当时我父亲看上去十分瘦弱,部队始终没有安排他上前线,后来前往解放区白求恩医科学校学习,随医院四分院奔波于华北地区战争前线,任副排级干部,做卫生员工作,穿梭在枪林弹雨中救治伤员,就此开始了他的部队从医生涯。
安阳解放后,我的父亲身着军装,随队驻留在安阳,医院。他曾是内科医生,听我母亲讲,那时他又黑又瘦,络腮胡须,习惯性驼背,像个老人。他治疗小儿腹泻很拿手,在当时,小儿秋季腹泻是死亡率很高的儿童疾病,由于他的偏方治疗快速有效,两三天治愈,所以很快成了名医,周边很多人慕名来找这名“老专家”,当同事们知道他们要找的“老专家”就是20岁出头的小杨大夫时,笑得前仰后合,这成了同事间常常挂在嘴边的笑谈话题,“老杨”从此就成为他的专有称呼。由于工作需要,医院放射科工作,才引出了日后的一段佳话。
年10月17日,我父亲杨朝山(最后一排右三)派往平原省汲县平原省干部疗养院的合影
全国解放后不久,年10月,省政府派数名医护人员前往平原省汲县建设平原省干部疗养院(平原省撤销后改名为河南省干部疗养院),我父亲被一起派往汲县(今卫辉市),为县处级干部待遇,当时他就是乘着大船沿着卫河来到了汲县,开始在汲县南门里天主教堂建立起疗养院,年11月,疗养院迁往辉县百泉,年,又迁回汲县徐庄北,在加拿大传教士医院时期的牧野中学校园内。这次是永久停留,也注定了他把一生都献给了这片热土。70年代,卫生部也曾调离父亲医院工作,但省干院坚决不放,此行未成。
疗养院的开拓者们来到汲县时,疗养院里疗养的干部很多,房子不够用,他们就自建房屋,自己动手挖地基,一砖一瓦盖起了多座平房。年9月,我父亲参加平原省医校X光诊断学习班。年4月,他又参加了上海市卫生局第一届放射科医师进修班,多次的培训学习,自己的专业技术有了大幅度提高。每当深夜,是他钻研业务的时间,凌晨1点之前几乎没有睡过觉,熬到天亮也是家常便饭。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夜猫子。
年9月,参加X光诊断学习班,杨朝山(最后一排右一)
我父亲十分耿直,说话从不绕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丝毫余地,这也许是他少年时,我爷爷对他的工作性质的严格要求造成的影响,执行任务必须圆满完成,没有任何可以推诿、变通,不能有半点差池。比如8点上班,12点下班,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必须的,8点之前必须到,12点之前一定不能下班,雷打不动。严于利己,宽以待人又就是他做人的基准。对感情他更是忠贞不二,解放后,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几乎每次运动母亲都会受到政治冲击,如右派、以及莫须有的三青团、地主身份和“站错队”,特别是文革期间,母亲住牛棚,被下放劳改,常常成为批斗对象。革委会找父亲谈话,要求我父亲离婚,否则影响政治前途。但我父亲始终坚定如一,掷地有声地回应:我比谁都清楚,她不是反革命,她是好人。就这样,家就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我们一家人风雨同舟,父亲始终不离不弃。
省干部疗养院收治的病人多数是战争中负伤或得病的县团级以上干部,一部分是在部队患上了传染病、肺结核和精神疾病的军官干部,不少病人还带着家眷和警卫员,所以这里病人个个都了不得,不好慢待。听母亲讲:有一位病人到了开饭时间,发现饭还没有做好,就问伙房的大师傅,大师傅毕恭毕敬的用卫辉话回答:阳晚儿都好了(意思:马上就好了)。饭做好了,还是老一套饭菜,几个专注等“阳晚儿(认为跟羊肉有关的羊弯儿)”的病人十分生气。大声呵斥道:“阳晚儿”那道菜怎么不上,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就是要吃“阳晚儿”!医院领导亲自出来解释:卫辉话“阳晚儿”就是马上、很快的意思。这才把这场误会平息下来。这里的病人康复后,有的归队了,长时间无法归队的或者原单位已经撤销的就成为疗养院的领导或职工了,包括官员带领的警卫员也都成了疗养院职工。抗美援朝期间这里又成为收治战场上负伤的 干部疗养院,不再限制县处级以下干部了。
由于治疗结核的经验丰富,年7月,疗养院成为河南省结核病院,医院全面对外开放,收治来自全省乃至全国的结核病人。我也成了少年,那是一个“谈痨(结核病)色变”的年代,结核病的死亡率很高。万不得已我也会到他工作的地方,每次去见他时,诊室里总是一屋子病人,特别到了夏天,汗臭味、脚臭味很大,令人窒息,再想想满屋子结核病人,令人恐惧。每天中午,错过上班时间就诊的患者无处可去,常常直接来到家里等候。我们吃中午饭,他们就坐在我家床上、凳子上等候,有时多达数十人,家人也会让一些熟识的病人在家里吃饭,其中很多是结核病人,他们在我家里也是习惯性随地吐痰,但我父亲从没有呵斥任何一个患者。一家人总是提心吊胆的,实则是有些恐惧。
那时的医疗检查设备十分落后,防护很差,胸部诊断,X光机就成为最主要的检查手段,透视和拍片都是那一台50毫安的X光机,我的父亲从来不在乎射线对自己的损害,在放射机荧幕前一次检查有时一呆就是几十分钟,为了工作方便从不穿带铅衣和防护眼镜,检查十分仔细。他的工作时间很长,一天要受到几个小时的放射线照射。他诊断X片有一个特别的技能,在全国也是唯一的,就是把X光片侧着看。那个时代,他曾多次发现了一厘米左右的恶性肿瘤,这在当时可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中国著名的诊断学专家李铁一和北京结核病防治所的放射科第一任主任(忘记了姓名,是否是他们一个人我无法考证)曾说:老杨看过的片子,我就不用看了。这也是对他诊断水平的最高评价(结核病院院志上也有记载),有时他们也会写条子请我父亲帮助诊断病情。后来我曾问过我的父亲是怎么看到这些肿瘤的,他说:当看到哪个部位有疑问时,我侧着看,会发现疑似部位有不平整的地方,这就极有可能比较凶险,通过X光机多方位观察,基本可以认定这个病灶有癌变的可能,再通过拉网等其他检查手段定性。我父亲病故后,我也求证了他的学生:为什么只有我父亲能看到这么小的肿瘤,难道他不教给你们。该学生说:“谁有胆量在X光机照射下,一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是要命呀。杨老师那么仔细通过X光机检查病灶,他看到的平片在他脑海里其实成了一幅三维图像”。他通过X光机动态检查,几乎会把每一个细节、哪一支气管下病灶部位都熟记在心里了。又有多少人敢在X光机前受X光照射近一个小时,并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此下去,他用敢于牺牲的精神换来的荣誉是常人无法超越的,无畏使他强大,专注使他安静,执着使他技术精湛,这就是我父亲一生的工作写照。
在酒精灯下制作肺导管
50-70年代,是谈痨色变的年代,肺结核病人死亡率很高,治疗空洞型结核病更加棘手,一是治疗时间长,难度大,副作用也大,二是结核病药物比较贵,需要报批进口。父亲想到如果将药物直接注入肺部空洞病灶部位,药物就会发挥最大疗效,彻底解决以上难题。如何将管子送到空洞部位,不仅要扎实的解剖知识,还要有合适的管子。由于当时中国的材料科学十分落后,为了能做成肺导管,每次出差到一个城市,必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当地的五金交电商店塑料管柜台,他会把最细的塑料管买回来,对比哪里生产的塑料管最适合拗制。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会在酒精灯下精心拉长、拗制各种弯曲度的管子,以便这些管子能够进入更细,更深的支气管病灶部位。就这样他成功发明了定向肺导管治疗空洞型肺结核技术,并出版了《定向肺导管》向全国发行。家里的那个酒精灯是他的宝贝,他绝对不让我们拿它玩耍。
还有,父亲多年来只要遇见典型病例,都会把X片子复制下来,加以留存,工作之余拿来审视,当作教材传授给他的学生。退休之后还常常翻阅总结,希望把这些宝贵经验留给后人,那些保存下来的病材至少有几十公斤重,有机会我会把他的这些遗物捐给院史馆,这些遗物是他的工作精神的忠实记录,展示给大家以勉励后来者再创医学奇迹。
年7月24日,我偶遇两位科主任,一个是骨外科的徐海彬,一位是原结核科的主任余光辉,他们原来都是二附院(医院)的医生,十分熟悉我的父亲,主动告诉我关于父亲的一些事迹:我父亲发明了X光断层技术,在当时是最先进的X光诊断技术,全省独此一家,在没有CT设备的情况下,就可以通过断层检查手段发现很多以前无法发现的病灶。还有就是我父亲在为病人进行肺导管治疗时,病人担心、恐惧,我父亲会拿自己先做实验,把肺导管插入自己的肺中,以消除病人恐惧。在全省的组织的防痨巡查中,每次X光透视,我父亲为避免他人受到X线伤害,都会让其他医生离开。两位主任告诉我:你的父亲一直是我们的榜样,也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他是医务工作者的楷模,是一附院精神的书写者,是一附院最高荣誉的保持者。
在医学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父辈们的成就也许现代人看来技术难度不大,甚至十分简陋,但在当时,无参考、无资料、无器材、无资金,能有做出几十年之后才发展起来的跨时空的技术,本身就是奇迹,不仅仅是质的飞跃那么简单了。如果说现在的微创介入手术技术改变了部分传统直视下的外科手术观念,我的父亲就是早期自主研发介入技术的拓荒者。虽然他们那一代很多医务工作者,学问不深、学历不高,但是依然在物资匮乏,信息闭塞,技术落后,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时代,创造了很多医学奇迹,为中国现代医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医院手写院志里的一张获奖证书照片
到年,为提高肺结核病诊治疗效,发明了局部滴注导管,并在临床应用,保证药物送到病灶处,收到了很好疗效,还编写了《定向肺导管》一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国,轰动中国整个医疗界。年分别获得汲县、新乡市、河南省劳动模范,并荣获文教卫体全国劳模荣誉称号,分别参加了县、地、省、中央群英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刘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获奖章一枚,荣誉证书一份,篆刻着“杨朝山”金星金笔一支及印有“杨朝山”烫金文字的毛泽东选集一套4本,周恩来亲笔书写邀请函,邀请出席与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的晚宴。
那时,见到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最高愿望,亲自接见更是无上荣光,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淡淡地说:毛主席当时在武汉视察,不在北京,周恩来总理转达了毛主席的亲切问候。
作者:杨永刚
编辑:段桂洪
本期编辑:弥庆宇
责任编辑:闫大海
觉得不错,请点赞↓↓↓
转载请注明:http://www.weihuizx.com/whsxs/58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