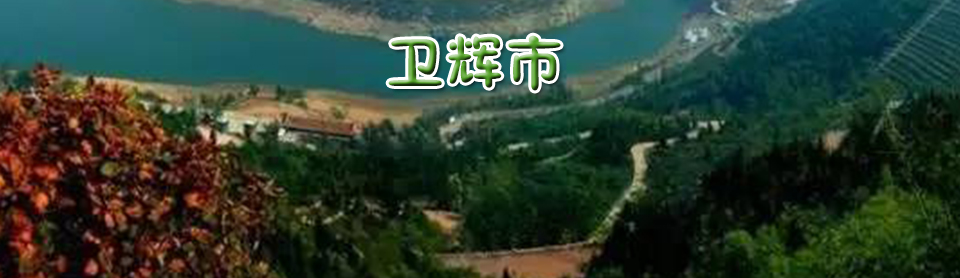微观卫辉彩和胡同的郭家不寻常出过知
◎郭自强
古城卫辉西关卫河码头,记录着这座城市热闹兴盛的光景。踱过德胜石桥,从德胜关的城门洞猫出去,便来到了府城北外城的桥北街。面和盐的营生,是这道街的风气和牌头。在德南街与卫河西岸的盐锅巷之间,横着一条不绰不狭、不长不短的老胡同,不错,就是彩和胡同。
彩和胡同大致形成于清代中后期,她曾经的主人是从南直隶大名府广平县而来的郭家。据口碑相传,郭家来卫的第一人名叫郭彩和,科举及第,皇帝钦点的卫辉知府,据说还干了两任。
郭知府育有四个儿子,家家都是大户楼院,一并坐落在现彩和胡同两边,四个家庭出入大街,知府大人上差乘轿子,抑或几大家子拴绑马车,必然需要足够大小的通道,这条胡同在这个节骨点便应运而生,因时任知府名叫郭彩和,慢慢的,卫辉城的老百姓便称之为彩和胡同。
那时的郭家,在卫辉可谓是一树红花,丁兴家旺,也算作盛极一时的豪门大家。但命运弄人,“富不过三代”的古理儿也同样应验在郭家人身上,应该从知府的儿子那辈,都迷上了抽大烟,纵是家财万贯也经不得这样折腾,变卖家产、家破人亡、门户败落只是连带而来的因果,难得留下一门血脉坚强地在卫郡存活延续下来,这便是我家。
想想那销声匿迹的三户,星火归于了尘,应无大的疑问,古时的人讲究的是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他们那般狼狈,故不堪返回直隶老家的面儿还是要大些的,剩下的极有可能就是自然地消弭于这世上。从我爷爷的父辈那里,就没听到过很往上那几辈子的家事了。
那就从我们这支仍旧生活在古城卫辉的家族说开去吧!些许关键的人和事,能够真实演绎世事沉浮和家族过往。
我们这一户,与盐锅巷(今严光街)上的何家住对门。这何家很不简单,寒儒之门出了两个争气的兄弟:何兰芬和何桂芬。手边有些史料的会了解,何兰芬给袁世凯做过军务采办,后来还做到北京崇文门总督,在正阳门也当过差。
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政后,便是通过他在北马市街购得地亩,建了袁宅,方才落脚到卫辉。也才有了之后王筱汀、李敏修等卫郡达人与袁世凯的交集。
我爷爷的爷爷,和他正是拜把儿兄弟。那时我们家道已经落魄,而何兰芬已经通过读书走出了家门。当时郭家人也深刻认识到吃光老本、坐吃山空这无以为继之路不可为,赌上残剩的全部家当干了两票“大事”:其一,按照当时说法,弄一两艘大帆船,往天津跑个来回,便能赚上足够的钱,对振兴家楣大有助力,便找了个郭家自认为非常可靠的人帮着跑船,谁料人心叵测,此人带着几艘船整出个中途跑路,从此人间蒸发了;其二,当时卫辉山中也已有煤矿开采,郭家努上最后一点家当,挖山开洞想做出点煤炭生意,结果工艺达不到,出现透水事故,还折进去几条人命。这可好,前前后后算上投资及赔命钱,这家当是彻底败光了,变卖了祖宗待了几代的产业,搬进了内城三拱桥附近的破庙里,沦为了那个吃人社会的最底端。
我爷爷的父亲,唤做老爷爷吧,名叫郭保胜,年生人,没长到半大,家境便已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因此,也没读过什么书,接受过什么教育。他曾经历了两件让他感到耻辱的事:
其一,保胜的父亲带他到顺城关的姨妈家去做客,这家家境尚可,据说儿子还在省城当官,小名唤作鹞子,谁知临走道别,前脚还没走稳,就听见那家人没好气的嘀咕“都这穷种,还好意思来”,父子俩顿感芒刺在背、无地自容,从此再也没攀过这门亲戚。
其二,稍后不久,保胜妈通过自己嫁到延津县东屯财主家的妹妹(保胜另一个姨妈),说给保胜找个活干,管口吃的都中。这次寄人篱下的经历起初还算愉快,保胜管放牛拾柴等轻活,有自己姨妈照应,倒也过得自在。
突然一日,财主家的牛耍疯,冲撞家仆,保胜顺手抄起棍子拍打了牛几下,好像把牛的眼睛捅瞎了,被财主得知后训斥了一番。大意便是“天天在家吃我的,喝我的,要不是恁姨,我可要管你”之类的话,保胜真是又怒又羞,那时应该应了“树要皮,人要脸”那句话,保胜负气之下,仗着一副好脚板,十来里路便回到卫辉城,见到父亲,诉说了各种委屈。做爸爸的当然心疼儿子,骂过财主后也犯愁啊,保胜你这把恁姨夫也得罪了,还能去哪?
思来想去,一个人的名字即刻回荡在脑海。对,就是他,何兰芬!听说他在北京给袁世凯当财政总长(当财政总长的实为周学熙;前文已叙,何兰芬任职崇文门总督,在正阳门管过事,亦算肥差),我跟他年轻时拜过把儿,你去投奔他试试?话罢,找出纸和笔有模有样的写了几笔,但见他在信封上重重写下何兰芬三个大字。期间,保胜只是不近不远地瞅着自己的父亲。
转眼,保胜坐火车来到北京。举目望去,京师太过陌生,人来人往,却没有一个亲人,心中的彷徨和不安很快跃上心头。保胜心里认定,找街头头顶上戴大盖儿帽的人,兴许就能找到何兰芬。抱着碰碰看撞大运的心理,保胜叫住了一个这般装束的人,说明想找何兰芬,那人倒也热道,“呀,找何兰芬,那可是大官啊,啥关系?”
没多久,保胜便被那官差领到了地方儿。容得通报后,保胜便径自奔向屋里,一进屋没走几步就对当堂之人响亮跪拜道“干爹在上,请受小儿一拜”,带来的书信由人递了上去,没多大动静,只听到堂上之人没好声地问道:“恁爹还没死嘞?”这可跟保胜原先预想的寒暄问暖完全不一样。
“你是郭XX(保胜父亲姓名未口传下来)他儿,叫个啥?”保胜简单作答着。
期间,何兰芬不无感慨:“我早都跟恁爸说过,他那过法不中,我来京城当官了,给他写信叫老哥哥跟我来享福,他也不写个信回回我;后来我又高升了,又给他写信,叫他来北京,还不回我话。现在家底败完了,想起叫他儿来找我了?”
“说吧,你都会啥?”
保胜答曰“没念过书”。
何兰芬笑道:“你看看,你这没读过书,不会写个字,我咋安置你,给外头说嘞,俺干儿哩,把你弄到个位儿上你弄不成事,那不是丢我哩人,弄个不好哩差事吧,这恁爹专门叫你来找我了。”想了想:“那样吧,你去总统卫队吧。”
至此,保胜终于算是安顿了下来,有好衣服穿,吃住也不愁了。据我爷爷提到,他父亲分别给袁世凯、段祺瑞当过兵,可能到最后也在队伍里混个小头衔儿。
这点与卫辉史志学者们关于袁世凯回京带走大量卫辉人充当马弁、警卫等服务人员的说法相互印证。那个时期,除了有袁世凯,卫辉人更有徐世昌,这两人可以说,是很照顾老乡的。
爷爷经常听他父亲提起在北京卫辉人有多“牙”。举个例子,在京城,保胜跟几个共事的进饭店,老板笑脸相迎,老客是哪的?保胜往往长枪一搁,一句地地道道的卫辉腔儿“恁爷是卫辉哩”,便砸向了老板的脸上。放在过去,抑或现在,在北京这种地方,敢这样说话,全赖袁世凯、徐世昌等人的面子啊……
保胜其实还是很孝顺的,每月能领可观的袁大头,而按照当时河南地价,一块银元就够在家的老爹置办足够田产了,何况是一月寄回去好几块,完全可以过上较为殷实的生活,无奈自己的老父亲郭XX早已“病入膏肓”,沉溺于鸦片的世界,至于何时终了,我的爷爷也没听他父亲细说过。
北洋时期,毕竟也是乱世。总统轮流换着做,小规模火并冲突在所难免,保胜也经历过一次现在电影里常出现的情节。我爷爷回忆,他父亲曾在北京街头算过命,这天天打仗的,问能活多久,算命的掐指一算,“放心吧,还得几十年活”。保胜听闻顿感愁云消散……
保胜也曾为一位没多少兵权的总统当过差。现在想想,估计是文治总统徐世昌,说是有一次冲突需要他们总统卫队也投入战斗,大家伙儿都吓得要死。总统卫队整日耀武扬威的,虽说也接受过训练,但跟仪仗队没啥区别,压根儿没打过仗。这九死一生的也不知道能不能闯过来,就看命硬不硬了!
在战斗中,保胜感觉自个儿胸口疼了一下,心想应该是被对方子弹击中了吧,恍惚之间用手摸了摸衣兜,竟翻出一枚被子弹打坏的袁大头,方才回想起那个算命的还真有些本事……
毕竟,相对于直隶人、山东人和安徽人,河南人、卫辉人在北京的根基还是太浅。随着袁世凯、徐世昌等人势力和影响的消亡,卫辉人犹如一阵秋风扫落叶般地纷纷返回故里。保胜也不例外。但据我的爷爷回忆,他小时候还见过他父亲时不时拿出压箱底的北洋军军装看,手抚摸着肩章的情景……
因常年在外,我的爷爷感觉他父亲结婚也比较迟,岁数老大了才娶了年生人、来自沿淀的母亲。郭家在卫辉已然无了根基,保胜索性带着在北京当兵时攒的钱,在延津东屯开了小卖铺,两口子倒也过了几年幸福日子。而后,正好保胜的姨表哥在陇海铁路上给人做饭,经其介绍,便换下戎装,穿着铁路制服上陇海铁路扳道岔了,这是个不需要满腹经纶的纯体力岗位。
保胜先后辗转宁陵、荥阳等地,并最终落脚荥阳,一干就是后半辈。这段日子,有几件事情值得一提。
其一,在东屯期间。有次保胜外出,有个二流子来小卖铺找麻烦,买东西不给钱,说话狂得很。媳妇回头告诉他,保胜一笑,让他来试试!毕竟在总统卫队干过,会一些拳脚功夫。爷爷母亲说曾见过,保胜能背对一面矮墙飞身蹦上,会些轻功,一日在店里正好碰见找事儿那人。保胜一看,那人面如土色、身材纤弱,好像一阵风就能把其刮飞。只听那人说道:“想当年,我跟恁爹熟类很,在卫辉城里的大烟馆儿都是老相识。”保胜一听气得要命,还在这儿给我说跟俺爹哩“交情”,抡起拳头佯装要打就给轰出去了,那人以后再不敢来。
其二,在国民党控制时期,已在荥阳车站呆了好多年的保胜曾经造成过一次“重大事故”,因疏忽大意未及时扳道岔,导致两趟车皮发生碰撞,车厢耸出铁轨老高,当时保胜也不知哪来的“二百五”无赖劲头,仗着自己跟站长(算是站上负责人吧)关系不错,一股脑将责任往站长身上推,这位站长的舅舅正是当时驻防郑州的国民党军队高官,且站长自己也老好人式的“揽过”,这事竟不了了之。
其三,毕竟常年在外工作,解放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把媳妇儿委身东屯姨表弟一家照应,每月往家里寄些钱,想让姨表弟帮着置办几亩地,将来退休了也有事可干。事实却是,他姨表弟将钱占为己有,也没咋帮衬嫂子,反倒经常把一家人的脏衣服扔到嫂子面前叫洗衣裳。保胜对此非常生气,正好赶上解放土改,姨表弟一家被划成地主,后果可想而知!保胜心里那叫一个窃喜,一生历经磨难和闯荡的保胜不由感慨,没想到共产党给我出的这口恶气啊!真解恨,不过事后想想,要不是这位贪心的姨表弟昧财,就凭保胜每月寄的钱要是全部购成地亩,最少也得弄个富农。结果到头来算作贫农,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呵呵。
只言片语:何兰芬,早先确实为袁世凯心腹,但因反对袁称帝,且在联名书上第一个签字,为袁所记恨,一日被人叫去说事,估计席间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或喝了不该喝的茶酒,身体一落千丈,自感时日不多,很快就去世了。他的族人也是遍布全国各地,我在卫辉的二姑夫就是他的后人,小时候都还见过家里的银筷子哩。
郭家和何家的后人百年后联姻,缘分这事,真说不了……另外,听二姑夫讲,年轻时曾去过安阳袁林游览,原本好好的天,突然阴云密布要下雨,就躲进了一个亭子下,不一会儿雨便停了,天又放晴。心想,袁世凯知道我是何兰芬的后人,可能也感觉当初非置好兄弟于死地,实属不义吧,下点雨慰藉慰藉我?
正如一种说法:袁世凯自比自个为“鳖精”,而鳖离不了河(何),这何兰芬被整死了,他袁大头称帝不久也一命呜呼了。另外何家置办的产业主要在张武店,号称良田四十顷,家大业大由此可见。
何家子孙其实还是挺争气的,我二姑夫的亲生父亲是河大毕业的,当时直接分配在省政府上班,年轻人非常优秀,但解放后政治运动太多,因不堪祖上的辉煌的“历史成分”疲惫身心,直接跳楼死了,他们何家便丧失了家门振兴的机会。现在想想,在那个年代,也是咱们卫辉籍人士在省城出人头地的一大损失。二姑夫的母亲年纪轻轻虽说过了阵富贵、体面的好日子,但出了这杆子事儿,也只能带着他们兄弟姐妹折返卫辉严光街老宅了,因生活困窘实在熬不过,改嫁了航运站一个楚姓师傅,孩子们也都改了姓儿。事后问为啥不等继父去世后再把姓氏改回来,二姑夫一家人感觉继父待他们确如己出,出于一片亲情就作罢了。据二姑夫讲,何兰芬还有后人在天津、长沙等地生活,他们前些年偶尔还略有走动……
⊙本号所转载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图片选自网络,如有侵权,请留言联系删除。文章不代表本号观点。
⊙合作请加(jyy-),投稿请发邮箱
qq.北京中科白癜风联合诊疗中心哪家医院看白癜风便宜转载请注明:http://www.weihuizx.com/whsxc/18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