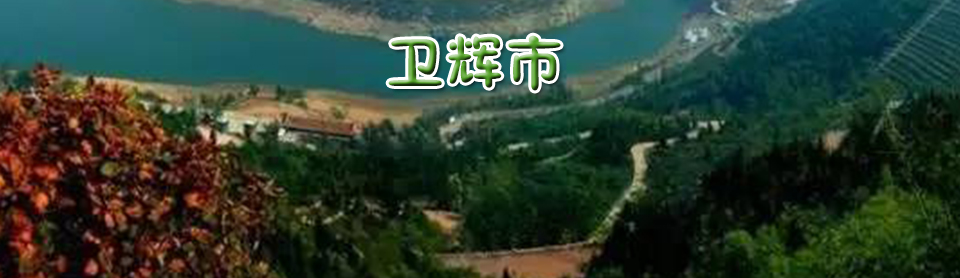南阳地名里的城市记忆,老南阳人你们还记得
城公园内,醒目的“宛”字
人与地间,有种内在的情感联结。你出生的地方、生活过的地方,即使有朝一日离散而去,你也会心中存之,忆之念之。
当然,这个地方是有名字的,想到听到或看到这个名字,曾经的一幕幕就会展现在眼前,或人,或物,或景,或事,即便是一堵爬满藤的墙,一段布着青苔的石阶,甚至是墙头开着黄花的仙人掌,都会因了这地名而变得情意深重。
然而在历史衔枚疾进的演化中,在因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伴之以地标的频繁更替中,尽管有的地名与历史一脉相承,但还有诸多老地名,有的消失,有的更名,有的被误传。也有一些老地名还在,但因其所在环境已不是最初的模样,其内涵便被尘封了起来,不少人说不出它的来龙去脉。
古宛城的地名亦是如此,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多少地名被淹没,多少地名被遗忘,又有多少地名被更替?还有那些被误传误读的地名、那些内涵已经休眠的地名,即使我们生活在这里,但,你真的知道它们的来历么?
地名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可触可感的地方历史,是今昔生活风貌的见证,甚至是乡愁得以栖息的枝头。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似乎都该了解它们,知道自己生活的这个地方曾有过的乡土乡情乡风乡韵;即便是那些在岁月里沉沉睡去的地名,也该轻声唤醒,让城市在一个个含有文化积淀的地名接续和传承中展现应有的温度和厚度,也让那些久别故土的游子,还能藉地名找到回家的路。
古宛城叫宛(wan)?错!应念宛(yuan)
身为南阳人,谁不知南阳古称宛呢?“宛(wan)”是常用汉字,但在特指南阳时,并不读wan,而应当读yuan。
据说五千多年前,神农氏遍尝百草为民选药,一日来到豫西南边陲一带(今南阳市辖区),见此地环境优美,一派葱郁,连声赞道:“此地真乃灵气宛(yuan渊)潜,富民宝地也,就起名叫宛(yuan)吧!”由此看,“宛”这个地名可追溯至三皇时代,可谓由来已久。春秋之初,楚国日益强大,灭掉申、吕后占领了南阳区域,楚文王根据神农氏这一传说,将此处定名为“宛邑”。
对“宛”字,《康熙字典》的注释为:“宛,於袁切,县名……秦为宛县。汉因之。明属南阳府。”年4月,再版的《辞海》将南阳古地名“宛”字的注音单列出来:“宛县(yuan渊),古县名,战国楚邑,秦昭襄王置县,治今河南南阳市……”
不知何时,古南阳的宛(yuan)被读成了wan。中国商务印书馆编辑部曾就此读音回复南阳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克锋时说,“战国古城宛,古时读yuan(於袁切)是肯定无疑的,wan(於阮切,碗)是它的另一个读音,表实词义,二者本不相干……《辞源》是一部重在溯源的古代汉语辞典,收字尽量反映古籍中的原始面貌,所以保留‘yuan渊’这个读音。”编辑部信中说:“厦门、荥阳等地名的读音,都有不从白读的趋势,即,不按它的常用音去读,保留自己的特殊性。在这一点上,宛字的读音却正好相反,是从俗、从白读的趋势,很特殊。”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宛(yuan)体现了南阳历史之久远、环境之优美,白读为wan,倒有点见笑于大方之家了。故曾有市政协委员提议恢复yuan的读音。只是,宛(wan)被叫了这么多年,是补偏救弊恢复为yuan好呢?还是约定成俗仍叫wan好呢?倒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尚待商榷。
南阳之名的由来,因地处伏牛山之南、汉水之北
古时的地名极易在改朝换代时被更改,但对我们南阳来说,秦汉时的“南阳郡”、晋代时的“南阳国”、唐代时的“邓州南阳郡”、宋代之“南阳县”、元明清之“南阳府”,不管“南阳”这一行政区域是大还是变小,“南阳”之名始终保留着。甚至隋代南阳郡郡治于穰(今邓州市),其名称仍是“南阳郡”。
“南阳”,最早见于史册是在战国时期,《战国策·西周策》载,“且魏有南阳、郑地、三川而包二周,则楚方城之外危”。《资治通鉴·周纪五》亦载:“秦置南阳郡,以在南山之南,汉水之北(即伏牛山之南、汉水之北)也”。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注释《资治通鉴》说:“凡山南、水北皆谓之南阳”。这就容易解释为何自古至今有多个地方叫南阳,皆因它们地势、地貌、地理环境基本相同:均处山南、水北。不过,有不少“南阳”在历史进程中更名,像春秋时期晋国之“南阳”(今我省修武县一带,处太行山之南,黄河之北)在元朝前就已更名。
为何南阳的“南阳”之名生命力如此坚韧始终未变呢?《南阳市地名志》曾刊有郑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孙重恩的文章,他在文中分析认为,南阳不仅具有山南、水北的特点,还有其地理、历史的特点:夏时南阳居夏人的腹地之南;商代的腹地是黄河两岸,南阳被视为商之“南乡”;周代则把包括南阳这块地方在内的广大地区叫做“周南”;汉《释名·释州国》中说“南阳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也。”由上可以看出,自三代至秦汉,人们使用“南阳”这个地名的“南”,都指南方而言,或是指国中之南,并非指一山之南,这一点和古晋国之“南阳”等有区别。
孙重恩说,自三代至春秋,“南阳”地区内封国林立不相统属,“南阳”作为一个大地区的名称未曾出现。直至楚向北发展打破封国林立局面,需要一个确能代表这一地区的地势、地貌和历史特点的地名,“南阳”于是应运而生了。事实上,也只有在楚占领了南起汉水、北至伏牛山南麓这块广大的盆地之后,才会出现这个统一地区的名称。此后,秦置南阳郡,这一地区扩大了,但以“南阳”二字,仍能很好地概括这一地区的地势、地貌、地理的相对位置及历史特点。
在孙重恩看来,“南阳”从一出现就是一个地区的概念,即伏牛山以南、汉水以北的这一广大地区的地理事物,而非一城一县的地理概念。南阳为南北交通要冲,各方面地位都相当重要,东汉时又有特殊的政治地位,“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产生活条件,且在使用‘南阳’过程中,通过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交往,愈来愈丰富着它的涵义,其名声也愈来愈显,这就使得‘南阳’这一地名不但不能废弃,且愈来愈具有重要意义,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和平街北端,曾有唐王府存在
民权街名字的变更,充满时代色彩
武庙坑,有坑,也曾有过武庙
净土庵,留下几多唐王府的传说
南阳,传说五千多年前被神农氏大赞为“灵气宛(yuan渊)潜,富民宝地”,自古为南北要冲。当然,历史上的南阳既受益又罹祸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天下有事,受祸最烈”,既饱受战争之苦,亦屡屡从满目疮痍与废墟瓦砾中站立起来重整繁华,有“四圣”之人杰,有“南都帝乡”之辉煌……
在兵燹与繁华的交替中,古宛城的历史缓缓向前,时光冲荡走城市许多细枝末节的记忆,亦留下诸多让我们可以凭吊或悠然遐想的痕迹——地名,就是其中之一。在采访和查阅资料中,我忽然觉得,地名不仅是方位距离或地理形态或祝福言志或上层建筑的具体化,有时,它简直是一个城市的身世,即便是某个历史阶段的一段身世,也足以让我们知道,这块土地上曾经的历史,曾留存的建筑,曾有过的人与事。比如,那些与唐王府相关的地名。
共和街
共和街在明清北城门内十字口东西两侧,这条古老的街道上,有我们熟知的已有多年历史的王府山——明太祖朱元璋之二十三子朱桱被封南阳为唐王时建的王府后花园假山。
我们都知道开封有龙亭,其实南阳曾经也有,旧址就在共和街上。当然,此龙亭非彼龙亭。据《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中记载,这条路东段曾建有唐王宗庙,名宗庙街,宗庙俗称龙亭,所以此段路又被称为龙亭(ma′r,与mang读音相近)。南阳的龙亭什么样?据说是建有高台,高台又建有雕梁画栋的宫殿式殿舍,四周有石栏,前面台阶正中斜以巨石,雕刻有龙的图案。
当然,与不少古街道一样,共和街东段这条路不光有宗庙街的名字,南阳民间文化学者郭文学说,共和街在明代称宗庙街。永乐年间建唐王府时,因无其地,以南阳卫指挥使司治改建为王府,南阳卫指挥使司则迁建于宗庙街指挥使鲍瑄旧宅。至清代,在明南阳卫指挥司旧址建成武庙,祭祀汉关羽、宋岳飞,街名改为武庙街;民国二十四、五年,国民党南阳县政府曾将武庙改作忠烈祠,改武庙街为忠烈祠街。
东段名字随着时代不同来回更改,西段则因有王府山的存在,称为王府山夹道。年,东、西段统一命名为共和街。如今,龙亭、武庙等皆了无遗迹,除了王府山默然驻守共和街,在共和街南侧,还有武庙坑这个坑塘以及它周围以武庙坑为名的小巷,尚弱弱地提醒着人们,这里曾有一座武庙存在。
和平街
和平街亦是一条古街道,不知为什么,看见这个街名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里的人们爱和平,也热爱家乡”的歌。也许,从其名字你就能猜出这应当是改过的名字,是的,这是它年改的“新”名字,取保卫世界和平之意。
和平街明代称通淯街,后因明藩唐王府建于该街北端,改名王府街。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记:“明王府在通淯街,永乐二年建。”民国十六年(年)曾更名维新街。该街旧时为石板路面,低于周边的街道,大雨时东、西、北三面的雨水汇流该街,向南注入护城河。年,街道作了整修,自北向南修建深2.5米、宽1.5米的砖券拱顶阴沟,解除了雨水排除不畅的威胁。
民权街
民权街就在和平街西边。这个带着时代色彩的名字,是民国二十年(年)国民党宣传三民主义时更改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明代时的民权街叫郾城府街,因明藩郾城王府在街北端而得名。依明制,亲王以嫡长袭,诸子封郡王,郾城王为唐庄王朱芝址之子。郡王每位盖府屋46间,还有前门楼、中门楼、前厅房、后厅房、厢房等等百数十间,虽比不上唐王府的宏大规模,想来也是气派非常的。
至清代,此街又改了名,据清光绪三十年《新修南阳县志·南阳城图》示,该街北段称廻龙街。民国时,则又改名民权街。
人民路
人民路不是古街道,而是年新辟建的道路。之所以写它,因为它牵涉到曾经存在过的柳河街和红桃街。
人民路中段原名柳河街,柳河街以北是红桃街的南段和万湾河(即梅溪河)的一段古道,其余为菜地。古道红桃街在梅溪河与西北角城河交汇处。据传说,明唐藩时梅溪河两岸分段种植花果树,栽种垂柳、柿树、桃树等,南阳因此有了柿子园、白果园、红桃街等地名。红桃街南北走向,南端在西关吊桥外与柳河街相接,北端于望乡台南侧东折至北关西拐街寨门。抗战时期,拆毁城墙,地形改变,街遂消失。
红桃街已然无存,甚至好多人已不知道它曾经的存在,不过,如今在梅溪河两岸,“里白果园”、“外白果园”的街巷名还在;文化宫街南侧,还有一条南北巷因位于旧时柳河街西边而被命名“柳河巷”。据说年人民路曾被命名为梅城路,年定名为人民路。这一点让我感到些许遗憾,“梅城路”,倒让人想起南阳“梅花城”之称哩!
净土庵
市区有净土庵社区,当然以前的确有一个净土庵存在,为南阳四大寺八大庵之一。
明代唐藩王府在紫山建有王府陵园,传说诸藩王每年到紫山陵墓祭祖后,在净土庵盥洗、清理尘土、休息回城。不过,此说法尚存疑,因为据说唐王府为免除从旱路去紫山扫墓之劳累,特意疏通万湾河河道逆流而上去紫山,想必他们回来时也会坐船顺流而归吧。
其他与唐王府相关的地名还有不少。记得我写了古城街巷后,便有人问起五福井的来历。五福井建于明嘉靖年间,这里曾有明藩卫辉王墓,墓前碑文载“卫辉五佛金井”一词,封建时代金井是墓的尊称,佛是王死后的尊称,故名“五佛金井”,后讹传为今名“五福井”。卫辉王为唐庄王朱芝址之子。当然,还有四福井,据清光绪三十年《新修南阳县志·疆域志》记载:“明承休、昭毅王墓在西北五里四府井,有嘉靖四十五年祭王妃王氏碑。”看来,四福井本名应为四府井。承休王,为唐宪王朱琼炟之子。
还有呢,七里园,古名“栖真园”,清光绪三十年《新修南阳县志·疆域志》载:“明赠唐恭王墓在城北七里栖真园。”《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文类·唐恭王墓碑》文记:“俄一疾薨正德丙子(年)七月二十三日也。年五十有四……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城北栖真园”。因距旧城北七里,故名七里园。
当然,还有葬着明蓬莱郡主墓的大庄,还有唐王府每年扫墓必经的腰站岗,等等。这些与唐王府相关的地名,少数沿用,大多数随着时代更迭、城市建设、地名指称的地理实体消失等更换了地名。而一次次地名的更替,记录下了历史的变迁与传承,它们就像一段段历史的碎片,串起来,让人仿佛听得到城市历史匆匆的脚步声。
转载请注明:http://www.weihuizx.com/whsxc/10069.html